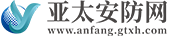今日热文:【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观看会泽另类大峡谷公园
解治龙 摄
 (资料图)
(资料图)
“相隔一座山,毕竟两个天。”在会泽县城,尚感春寒料峭,到了距离会泽县城仅有30公里的布多村,却也酷热难当。
3月24日至26日,陪同摄影家一行到布多—小江大峡谷拍摄,追光掠影这一片巍峨豪迈、壮美苍凉的土地,千古江流、空谷回音的峡谷景观,即便不是第一次造访,却也又一次被震撼。
金华春 摄
崔庆坤 摄
泥石流地质公园
河流作为非常活跃的外营力,对地表具有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由此形成千姿百态的河谷地貌,对人类居住环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会泽山高水低,峡谷幽深,雄峰突起的壮美景象,在布多—小江大峡谷,有着最为直观的体现。
从海拔4017.3米的乌蒙山主峰牯牛寨到850米的小江村,这样的海拔落差,仿佛一个性格偏激的人在走极端。发源于大海草山景区门口附近的河流从小江村龙潭河注入小江,地貌也从繁花铺就高山草甸跌落到草木稀疏的干热河谷。“山高一丈,大不一样。”小江、大海梁子等地气候呈垂直分布,常常是:“山脚赤日炎炎,酷暑难耐;山顶云雾缭绕,寒气袭人。”大海乡五月飘雪、七月飞霜的气候屡见不鲜。“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这正是峡谷旅游的魅力所在。
峡谷自古就是天然通道,是人们联系的纽带。有专家称小江峡谷范围内为“天然的泥石流博物馆”,更形象地说,是一个“泥石流地质公园”。
崔庆坤 摄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张云林 摄
张云林 摄
徐汝枞 摄
没有苍凉悲壮的底色,就不是泥石流地质公园。
在巍峨的崇山峻岭间,斗折蛇行的山间公路就像是一条条白色的绸带,弯弯扭扭地系着大山和农舍,翻过一座座山梁,一阵阵山风吹过,一座座大山紧紧地夹着宽宽的河滩,树不长,只长着枯黄的杂草,长着涂满绿色的村庄。光着身子的山峰、山峦、山腰、山坡、山沟,山谷、山脚,如同一群群脱得浑身精光的汉子,裸露自己的一切,累累伤痕触目惊心。地表径流对山坡和沟床持续不断地冲蚀掏挖,山体常常崩塌滑坡。那些流淌出来各种各样的泥土沙石,从山顶顺着山沟倾泻下来,像染了颜色的伤口一样,肆意地涂抹着大地,冲向河滩中。被地壳运动撕扯开的五脏,磷矿、铜矿、铅锌矿就是打翻的颜料盒之中的天然涂料,赤、橙、黄、绿、青、蓝、紫,五彩缤纷,色彩给人视觉上的强烈冲击。汽车沿着钱家梁子崎岖山路行驶,忍受着心跳加速和小腿发软。眼前空旷一片,正是高山峡谷,已临万丈深渊。俯瞰峡谷,险峻异常,从山顶到谷底,垂直距离总在数千米之上。跌宕起伏、厚重深邃的沟壑排列其间,越是靠近谷底的地方,越显现出破碎的地表和裸露的岩石。
崔庆坤 摄
解治龙 摄
王华 摄
徐汝枞 摄
布多河谷风光堪称地理奇观,山势陡峭,峡谷纵深,有人工修造的小段“红旗渠”,从悬崖上穿过的“挂壁公路”;绿洲、河谷共存,绿洲充满生机,一片富庶丰饶的景象;泥石流冲刷切割形成的峡谷是如此的险峻、荒凉而悲壮。如此大的地貌反差,给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感觉,无论是报刊杂志上,还是网络媒体上,多少摄影人关于泥石流地质地貌的摄影作品,反映的大多是东川境内阿旺河到小江入口格勒一带的宽阔河谷的地质地貌,除了大面积泥石流堆积的青灰色泥沙之外,远没有布多河谷这样险峻和悲壮,也没有布多河谷这样地质地貌上丰富的色彩。
第二天下午,汽车沿着峡谷边缘挂壁的崎岖山路行驶,山沟的两面,是高耸入云的绵延山峰,山脚与河床的连接处,一条蜿蜒的白色河道从山谷上游的两座大山形成的缝隙间冲出来,犹如超级巨蟒在山间游动,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从山上滚下的各种乱石烂泥塞满了河滩。宽敞的河滩除了中间有一条浑浊的流水外,整个河流都被一条条从冲沟里奔来的泥石流冲得乱七八糟的,那些泥石流所到之处,山和土地都像被无数的钉耙抓过一样,堆积着青灰色泥沙。
李永星 摄
王华 摄
没有磅礴雄浑的气质,就不是地质公园。
蒋家沟,与金沙江支流小江垂直的一条山沟,因多发泥石流而闻名于世,是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地质奇观之一。大海乡泥得坪村左边1公里就是蒋家沟泥石流遗址。《一次大型的泥石流》这篇曾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章,详细记录了1977年7月27日在东川境内蒋家沟发生的一次世所罕见的大规模泥石流,读起来惊心动魄。
据资料显示,小江流域地区常年爆发泥石流的山沟多达113条,造成程度不同的地质灾害。爆发规模大的时候,泥石流总量可达37万立方米;延续的时间可达12小时;最大瞬间“龙头”流量高达2400多立方米每秒;在坡度6.5%的谷地中,最大流速竟达15米每秒。这样爆发频繁、规模巨大的泥石流,在我国其他地方是罕见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据说,蒋家沟由于泥石流的冲积填埋,沟床已经抬高了100多米,形成了一片冲积扇面。
在那些记录灾害的镜头中,泥石流所到之处,有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由石头、泥浆组成的泥石流起初像一条巨蟒,缓缓地蠕动着,不见波浪不见波涛,却如波似涛地越来越快滚动而来,组成了一条如同铁水那样虽然看不见烈焰,却比铁水烈焰可怕得多,恐怖的暴戾之河,在这股暴戾的力量面前,成吨的甚至是几十吨重的石头,在泥浆的推动下,一切阻碍它的东西都会被它轻而易举地吞噬和搬迁,那情形就如黄河里移动的浮冰一样,凡是所遇之物,没有不被泥石流吞没的,严重的时候,整条小江完全被泥石流所淹没。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在河床的中心,依然留下了泥石流的痕迹。被泥沙掏挖而崩塌的纵截面依然还在,碎片状的石块铺满沟底,已被清洗得干干净净,阳光下放着耀眼的白光。含泥量很高的流水还在涓涓流动,这一切仿佛还在讲述着那一段惊天动地的泥石流的故事,也仿佛还在警示着人们。
这是一种原始的粗犷的美,这是一种气势磅礴的美,更是一种融进血液的惊心动魄的悲壮的美。
李永星 摄
李永星 摄
王华 摄
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就不是地质公园。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公路十八拐。道路是在悬崖上凿出来的,公路是挂在悬崖上的,美其名曰“挂壁公路”。即便是在今天车子普及的时代,没有精湛的车技和足够的勇气,是万万不敢上路的。薄刀坡,顾名思义,薄如刀口的山坡,是布多进出东川和途径温泉,进入会泽县城的唯一通道,在宽不足一米、陡峭的坡顶上下行走,这是何等的艰难。行路难,开路更难。昔日人背马驮的岁月,与天斗、与地斗,祖辈的梦想在彩色的土地上播种,子孙的汗水渗进红色的土壤。经年累月,用双肩托起沧桑的日月,靠双手推动命运的辘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泥石流相伴,与土地为生,整日辛劳,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威胁,漠然置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这是一种象征着顽强生命力的美,天地生养万物,劳动改变世界。就是这一溜溜沟沟,就是这一道道坎坎,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山人,在大山的孕育下,养成了大山一样的性格:山一样的淳朴谦逊,山一样的质朴厚道,山一样的粗犷豪放,无论男女老少,具有着和大自然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同时他们也有着对外面美好世界的向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千百年来,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广大农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田园风光,不愧天人合一的劳动成果;农艺丰碑,堪称乡愁难忘的精神家园。
崔庆坤 摄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金华春 摄
金华春 摄
李永星 摄
李永星 摄
李永星 摄
李永星 摄
徐汝枞 摄
王华 摄
王华 摄
王华 摄
金华春 摄
王华 摄
王华 摄
徐汝枞 摄
张云林 摄
张云林 摄
与泥石流抗争的村庄
在这个地质公园的范围所及之处,分布着迥然各异的村落,呈现出不同的聚落景观,仅以布多、温泉、小江三处就可窥见全貌。
布多,一个被称为“船”的地方,一个1400多人的村庄,素有“金布多”之称。《云南省会泽县地名志》是这样诠释布多:“彝语布:刺猬,多:有或在,即有刺猬之地。”这里地势险峻,沟壑纵横;土地肥沃,田园锦绣。站在高处往下看:绿油油的田园,整齐有序的村舍,袅袅升起的炊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数丈深、宽十多米的二道沟壑,把原本一个完整的村庄深深切开,犹如跌落在荒漠中的一片绿叶。
金华春 摄
金华春 摄
走进布多村,充满生机,春意盎然的田园风光映入眼帘,迂回环绕、层层叠叠、色彩斑斓的梯田种植了诸多作物。大片大片的青绿,充满着无限生机,也传递着浓浓的春意。麦子已经抽穗,蚕豆已经熟透,稻秧已经拔青,整个农田都已进入了小春季节,农民们也准备好了下田割麦、收蚕豆、犁田使耙、栽秧的动作。村民赶着一群群牛羊穿村而过,清脆悦耳的鸟叫声和鸡鸣狗吠声萦绕其间。稻谷、花生、甘蔗、红薯、石榴、柑橘,这些世代居民长久耕作的作物,交错搭配,挥洒五彩之色,犹如上帝打翻的调色板一一色彩斑斓的梯田。依托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些农特产品也能够及时外销了,变成商品。
历史上,布多村在行政级别上是布多公社,今天的温泉村属布多公社辖区。地处小江断裂带上的温泉村,得名于辖区东面山腰的一眼温泉。周围被巍峨的大山环绕,大山脚下一片较为平缓的地方便是温泉村村民居住的地方。明清时,因东川采矿业的兴起,“热水塘”便是铜运要道上一个重要驿站。曾经的“热水塘”,绿树成荫、风景宜人,是会泽十景之一 “温泉柳浪”景致所在地。曾有官办“官塘”“男塘”“女塘”和亭、台、楼、榭等休闲设施,热闹非凡。近代云南著名学者、云大中文系教授刘尧民先生曾为温泉柳浪赋诗一首:“云外桃花楼外楼,汉南种柳可维舟;一泓春水湿如玉,难洗人间万斛愁。”
王华 摄
徐汝枞 摄
温泉村是处于“泥石流地质公园”边缘的村庄,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在村民居住的下方,一条纵深狭长、伤痕累累的沟壑与小江相通。地表破碎,岩石裸露,植被稀少,除了山间极少的松树之外,山腰便是一些杂草和灌木丛,靠近谷底的地方是满眼裸露破碎的地表,属典型的泥石流地质特征,雨季天泥石流造成的塌方被清除在公路的外沿,这些塌方的泥土和碎石,用手触摸,极其坚硬,人们用“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包糟”来形象说明它的地质特性。
崔庆坤 摄
解治龙 摄
解治龙 摄
李永星 摄
徐汝枞 摄
张云林 摄
张云林 摄
沿着河谷向下行驶10余公里,到了小江村,山坡已然没有了斧劈刀刮的裸露,绿色已经涂满了山坡与沟底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已是成片的芦苇,芦苇和河床之间,散落的是新垦的农田,玉米、大蒜、白菜或洋芋,在泥石各占一半的土地上生长着,正如这片红土地上生长的不屈而坚韧的人们。
小江共有大石坪、白沙坡、小江、赤落沟、二坝田、桃树角、窝布嘎,以及村委会驻地八个自然村。历史上的小江曾经有富庶丰饶的村庄;经年累月,由于植被脆弱,泥石流的破坏,这些村庄或在沟边,或悬挂在悬崖上。
地名作为人们依其主观认识,共同约定而赋予客观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一种代号或标记,乃是一种典型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它是一个地方历史的见证和记录,地理特征、地质地貌的指示牌,也是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颇具特色农业景观。
李永星 摄
徐汝枞 摄
崔庆坤 摄
崔庆坤 摄
李永星 摄
解治龙 摄
李永星 摄
李永星 摄
赤落沟和窝布嘎均为彝语。赤落沟也叫至落沟,“至落”意即谷田,谷田边的沟,在深山峡谷中的赤落沟现在仍有一定规模的稻田;“窝布”为彝族人名,“嘎”彝语为村庄,窝布嘎为窝布家居住的村庄。窝布嘎在小江村委会东边的沟坎上,利用高山水源,灌溉着一片梯田,梯田四季常绿,悬挂在沟坎上,这片绿洲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流逝。虽然勉强从沟底打通一条通往村庄的简易公路,但坡陡弯急。村庄后面植被稀少,遇到大雨,多少人家出现不眠之夜,时常提防山上的泥石流袭来;进村道路,沟渠全部冲毁,村庄经常出现孤岛局面。
李永星 摄
解治龙 摄
任礼俊 摄
白沙坡小组坐落在大山脚下的山坳里,村庄后面裸露的荒山,一片白花花的流沙仿佛流动一样指向村庄;大石坪,顾名思义,建在一个石漠化的坪子上,村庄中七零八落的一些植株从石头的缝隙中扎进山体,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两个村庄周围看不到半块可以用来耕种的土地,两个自然村只有依靠村庄前面尖山河里的沙坝来维系生活。勤劳聪明的村民在不断改造沙坝,先推平一块沙坝,四周筑高围拢,留一个进水口,让水带进淤泥,淤泥沉积后,在上面种上稻谷。若是遇到沙滩洪流爆发,所有辛劳化为乌有。
李永星 摄
徐汝枞 摄
解治龙 摄
金华春 摄
李永星 摄
李永星 摄
王华 摄
解治龙 摄
小江自然环境恶劣,这里十年九旱,滑坡、泥石流在本村区域不时出现,群山奔涌,千沟万壑,村庄就在大山脚下,山上一片荒芜,难有绿色呈现。近年来,沟谷中种植了耐旱的桉树,其余都是一撮子秃山。早已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这些村庄,恰好遇到会泽10万人扶贫搬迁项目,在政策的引导下,主动迁徙200余户农户,也为留守的100余户村民腾挪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小江集市是周边村民集中交易商品的地方。低热层是小江的天然温室,发展早冬蔬菜和热带、亚热带经济林果得天独厚;西瓜、黄果、柑橘成了小江的一张名片,冬早蔬菜已成为市场青睐的品牌。
李永星 摄
小江峡谷还保留着运铜和商旅往来的通道;还有一段红色故事。小江为当年从矿山运铜到东川府治所在地会泽的必经之路,枯水季节,运铜马帮和矿工从铜厂涉过小江,沿尖山河谷而进,在尖山住店,第二天经尾坪子直抵会泽。1935年5月4日,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在攻克会泽县城后,一路向西,西渡金沙江。从今天温泉村的大村子一直到小江口都有红军的宿营地,先头部队就在小江口、大石坪宿营,当时红九军团的主力部队就经过这条线抵达树桔渡渡口,渡过金沙江。
崔庆坤 摄
金华春 摄
解治龙 摄
地老天荒,沧海桑田,时序交替,亘古如斯。如果你想真正体味苍凉粗犷、雄浑壮美的泥石流地质公园奇观,体验低热河谷的天然桑拿,踏访蒋家沟泥石流遗址,那就不妨到布多—小江峡谷一游吧!因为,布多—小江峡谷,它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也是很另类的!(陈晋 徐汝枞)
X 关闭
精心推荐
Copyright © 2015-2022 亚太安防网版权所有 备案号:沪ICP备2020036824号-11 联系邮箱: 562 66 29@qq.com